注册新用户
- 登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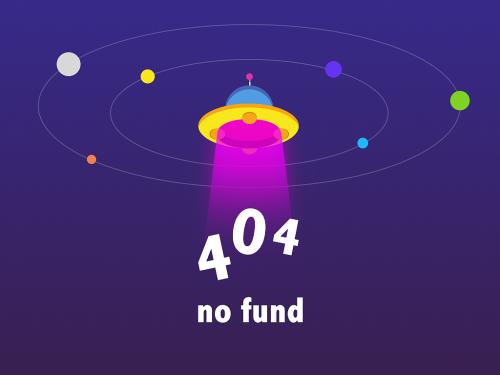
注册新用户
修改密码
马尔克斯说,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,而是你记住了什么,又是如何铭记的。
自儿子出生以后,我的时间丈量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。儿子出生在八月,于是我的年轮周期便以八月为始进行推算。
在过往的一个多年岁里,很多人陆续擦肩,很多事走马而过。如同棋局,一局过后便又重新洗牌,输赢归零。但终归还是有一些事,镶嵌在记忆的长河,每每想来,补丁摞上补丁,带着思维的温度,掺杂着滚烫的眼泪。 正如这座城市的街头,每天都有很多背对人海、逆着光亮掩面而泣的人;不是因为脆弱,而是有些疼痛,来不及躲避就要汹涌决堤。
50公里的道路有多长?长到无边无际、没有尽头。
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,我带着儿子前往隔壁的x城急诊。一路上为了追赶时间,马不停蹄。母亲与妻子焦灼不安地坐在后排,轮流怀抱着浑身滚烫、近乎昏厥的儿子。导航在驶出高速后犯了浑,将一家四口径直引入无人之境。路面是坑坑洼洼的施工现场,仅不足半幅得以通行。没有人声,不见灯影,车灯的光线亦被漫天的扬尘所覆盖。
在黑漆漆的乡间公路上,母亲的颈椎病不胜颠簸,终究没有忍住,于后排呕吐不止。妻子慌忙接过拥在母亲怀里的儿子,我也紧急踩住了制动。在道路明晰之前,我示意母亲下车休憩,呼吸新鲜的空气,活动僵硬的筋骨。她理了理衣衫,以毛巾掩面,装作若无其事,并执意要求我分秒必争。
那一刻,我陷入了两难的困局,并渴望着山重水复后的柳暗花明。只能屏气凝神、手心捏汗,任车轮在细碎的砂石上摩擦。
后来,我们一路冲出坎坷,走向了光明。孩子也逐渐好转,恢复了往日的生气。只是那一路遥远,让我更加明了肩膀的重量。我怕自己努力的脚步,敌不过父母变老的速度,赶不上孩子成长的节奏,而立之年所有的追逐与向往,都逃不过责任。
我向来无心感知孩子成长的速度,直到某次带他在游乐场中玩耍,看见他站在众多孩子的中间,个头远远超出其他玩伴,让我可以凭借着身高就能轻易找到他的位置。并且他已能够从容地表达自我,在众多幼童中逐渐有了兄长般的号召力。
那一幕发现过后,我于脑海中开始了一段记忆回放,但能够搜索到的画面信息实在太少。前者还是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抱在怀里,为他笨手笨脚地去换一片尿不湿,以及不小心打翻了奶瓶。后者便是他已经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,在校园里认识很多新的朋友,以及眉宇之间有了清晰的轮廓。
当我把自己的那份惊讶告诉妻子时,引来了她的深情埋怨。你啊你,整天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只会坐享其成,开心了逗一逗,忙起来对孩子连一句话也没有,怎会知道养育孩子的辛苦?
有一种父亲被称为别人的父亲,有一种老公被唤作别人家的老公。对于孩子,我可以买来许多心爱的玩具,却无法抽身陪他痛快地玩耍;我可以送他五颜六色的绘本,却没有安静地给他讲过一个完整的故事;我可以勒紧腰带给他区域内优质的教育,却无法亲自送他走一段求学的路。
“妈妈,今天又要把我送到哪里去?”这是在妻子因工作无暇照料之际,儿子时常发出的困惑。这一问,像匕首直抵胸腔,每每忆起都让人溃不成军。
去年的初冬,因身体抱恙,我挣扎在医院的床榻上,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台手术。那一日清晨,我早早换上了手术服,像是枕戈待旦即刻出征的勇士。
我给自己鼓足了劲,在走进那扇沉重的手术室大门之际,我对身后的家人和年幼的孩子回头留以微笑,然后径直步履轻松地走向冰冷的深处。
在充满福尔马林的密闭空间里,有一小股寒流沿着脊背蜿蜒到了腰身。我裸露着胸腔,尽力汲取着无影灯的温暖。我朝着麻醉师双手合十状,便顷刻进入了梦乡。
那一梦过后,换来了我的重生。我充分感受到活着的美好以及存在的价值。即便是身上多了几条细长的管子,有间歇性的浑浊液体自体内溢出。
也正是那场难忘的经历,其间包裹了两个秘密。一个是家人善意隐瞒了术中病理的结果,不过后来也被术后病理所推翻。一个是我早早地写下了一封当时可视作遗书的东西,隐匿在钱包的夹层深处。只是这封信于我醒来过后,便失去了它所有的意义。
在那场手术之前,我曾抱着无比侥幸的心理,前往大城市的医院复诊,渴望能有良方使我不必受切肤之苦。但结果难如人意,拿到确诊书的那一刻,我竟胆小得像个遇上洪荒猛兽的孩子。
从医院出来,我和妻子单独走了很长的路。后来在静安寺附近的街心花园里逗留。我对妻子说,走吧,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这座城市,回到我们本来的地方,那里有我们的挚友、双亲还有孩子。
饥肠辘辘的傍晚,在那座城市的灯红酒绿即将来临之前,我和妻子拼命追赶时间,朝着几十公里外的火车站进发。为了照顾我的情绪,她主动抢过我手中的行李,亦步亦趋地跟在我的身后。期间我转身瞥见过她憔悴的面容,迷离的眼眸深处泛着泪水的光泽。
在一路向北的午夜火车上,我和她相视无言,谁也不忍多看谁一眼,更不知接下来会怎样。偶尔透过车窗依稀瞧见,对方的眸子深处已是一汪清泉涌溢。后来在离家更近的地方,她压抑已久的内心再也把持不住,埋头便是一阵歇斯底里。
列车驶过南京,夤夜的古都洗尽铅华,万家灯火只剩点点星光。我试图岔开话题,聊起了孩子的种种趣事。她定了定神,自顾自地给我宽慰。她让我不必有过重思想负担,即便是倾家荡产,也要陪我遍访名医、求得仙丹。
我明白这点小病大可不必,但还是忍不住冲破了泪点。那一夜,我哭她也哭,谁都不再给谁安慰,只是翘首盼望着天亮,回家抱一抱孩子。
编辑:文潮